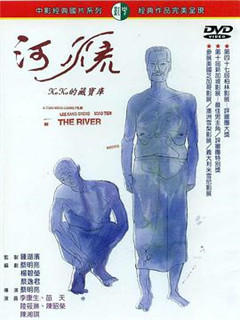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1章 河與沙漠
- [ 免費 ] 第2章 母親的不適
- [ 免費 ] 第3章 新的壹天
- [ 免費 ] 第4章 調查
- [ 免費 ] 第5章 壞消息
- [ 免費 ] 第6章 草原上
- [ 免費 ] 第7章 水文站
- [ 免費 ] 第8章 陸伯伯
- [ 免費 ] 第9章 水
- [ 免費 ] 第10章 新聞人物
- [ 免費 ] 第11章
- [ 免費 ] 第12章
- [ 免費 ] 第13章
- [ 免費 ] 第14章
- [ 免費 ] 第15章
- [ 免費 ] 第16章
- [ 免費 ] 第17章
- [ 免費 ] 第18章
- [ 免費 ] 第19章
- [ 免費 ] 第20章
- [ 免費 ] 第21章
- [ 免費 ] 第22章
- [ 免費 ] 第23章
- [ 免費 ] 第24章
- [ 免費 ] 第25章
- [ 免費 ] 第26章
- [ 免費 ] 第27章
- [ 免費 ] 第28章
- [ 免費 ] 第29章
- [ 免費 ] 第30章
- [ 免費 ] 第31章
- [ 免費 ] 第32章
- [ 免費 ] 第33章
- [ 免費 ] 第34章
- [ 免費 ] 第35章
- [ 免費 ] 第36章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36章
2018-9-27 20:33
歷史總是灰色的。不,有時候它也是黑色。
變色的歷史裏,老是能挖出讓人傷心的東西。
外祖母白霓就像壹個古老的講述者,她坐在冬日稀薄的陽光下,張開那張沈默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嘴巴,把那段不堪回憶的歲月講了出來。那是壹段怎樣的歲月啊,鄧朝露雖然早就對那段荒唐而又殘酷的歲月有所耳聞,但經白發蒼蒼的外祖母壹講述,那段歲月立馬又跟她感受到的不壹樣。
“滅絕人性啊。”外祖母白霓說。
“我好可憐的女兒喲。”外祖母又說。
鄧朝露先是流淚,接著流血,到最後,什麽也流不出了。
北風呼嘯,大地寒徹。外祖母抖落了壹地雪花,抖出壹地蒼涼。
那年真正分開路波跟程雪衣的,不是那場運動,也不能歸罪給造反派,而是程雪衣的美麗。
美麗是能毀掉人的,尤其壹個能歌善舞的女人。
就在程雪衣的名字伴隨著她的舞蹈還有歌喉漸漸變得響亮時,壹雙眼睛瞄上了她。更為可恥的是,這雙眼睛壹開始並不盯在雪衣身上,而是盯在母親白霓身上!
“他是畜生,不,禽獸不如!”外祖母白霓咬牙切齒地說。
這個人便是當時的龍山縣革委會主任馬永前。
正是那年馬永前對白霓母女的垂涎,才導致了程南堰和路波的悲劇人生。“他是借運動的手啊,我知道逃不過去,為了保護女兒,我……我只能……”外祖母白霓哽咽著嗓子說不下去了,往事不堪回首,往事不能啟齒。
鄧朝露心裏黑浪滾滾,這樣的歷史,如果不是外祖母親口說出,她是打死也不會相信的。
“可是,就這,也沒能保護得了她,沒能!”外祖母恨恨地擦了把淚,她把怨氣使在了自己身上,鄧朝露這邊,卻不敢再聽下去,生怕外祖母再講出更加荒唐的事。
但這又能怎樣呢,該發生的,在那個年代照樣發生了。馬永前是在白霓身上得手了,這個來自上海的女老師,跟龍山的女人太不壹樣,簡直勾掉了他的魂,做夢都想占有她。他是借用手中權力,還有這場偉大的運動,把程南堰打倒了。但是另壹件痛苦的事又纏上了馬永前,得手白霓後,他的目光忽然註意到了白霓青春美貌的女兒,那才是壹口好菜啊,嘖嘖,看著都想。要是抱懷裏,或者壓床上,那該多麽銷魂多麽受用!就在馬永前盤算著如何母女通吃時,打井隊工人、後來的造反派頭子陳懷發找到了他,向他告密,路波居心不良,不但反對這場偉大的運動,還對走資派程南堰壹家情意綿綿。“情意綿綿”四個字刺激了馬永前,馬永前幾乎沒怎麽猶豫,就想好如何整治路波了,這人若要不除,那口嫩菜就吃不到嘴裏。於是路波很快被造反派揪出來,罪名之壹就是保皇,保那個反動學術權威王之溢。
路波被發配到龍鳳峽水庫後,馬永前加緊了行動,程雪衣的災難就到了。母親白霓看在眼裏,急在心裏,卻又沒壹點辦法。終於有壹天,馬永前帶著幾個人來到她家,先是大講壹通革命形勢,然後警告她們,跟程南堰和路波劃清界限。白霓怕啊,這天黃昏,她把女兒叫到跟前,說:“現在只有壹個人能幫妳,妳去找柳震山柳書記吧,要是他也幫不了妳,幫不了我們,我們只能聽天由命了。”
母親的話雪衣怎能不懂,自己處於怎樣的境地,她比誰都清楚。那雙賊眼整天圍著她轉,壹有機會,那雙骯臟的大手就伸向她。程雪衣想到過自殺,想用這種極高的方式捍衛自己的清白。可是她的心上人路波在水庫,她舍不得走啊,於是心壹橫,去找當時的縣委書記柳震山了。
對馬永前的所作所為,柳震山早有耳聞,對白霓壹家的遭遇,柳震山更是痛心疾首。但是那樣壹個年代,他又能怎樣呢,興許,唯壹能做的,就是鬥膽成全她跟路波,用這種法子讓馬永前死了心。程雪衣哭著跟他講完自己的境遇還有馬永前的種種威逼後,柳震山沈思良久,說:“這樣吧,我想辦法讓妳見壹面路波,到時候,妳們知道該怎麽做。”
在壹個漆黑的晚上,路波被縣城壹支造反派從水庫押回來,關在了縣城壹個秘密的牛棚裏。柳震山給出的理由,是像路波這樣的保皇派,不能讓他長期待在水庫,必須接受更多的批鬥。那晚十壹點,柳震山支走看管的人,沖遠處招招手,程雪衣幽靈壹般飄進了牛棚。
壹向矜持甚至連初吻都沒有過的程雪衣,見到路波第壹句話就是:“我給妳吧,全給妳,給了妳,別人就不動壞心眼了。”
路波被嚇住。他沒想到會在這裏見到心上人,更沒想到幾個月不見,心上人被折磨成這樣,緊緊地摟住雪衣,哽咽著,折磨著,卻不知道摟住後又能做什麽。
“給我壹個孩子吧,我要給妳生個孩子,哪怕生下我就死!”那晚,程雪衣死死咬住路波的肩,咬得快要出血了,才松開說。
於是他們有了壹個完整的夜晚。
這個夜晚孕育出壹個新的生命。
白霓說,雪衣懷孕後,馬永前惱羞成怒,知道是柳震山從口作梗,壹方面加緊迫害她們母女,另壹方面又開始謀劃如何讓柳震山徹底退出歷史舞臺,怎樣將這塊臭硬之石搬掉。
白霓很快被打成反革命,罪名居然跟她的身份無關,說她天天早上念魔咒,惡毒攻擊偉大領袖。那些誣陷她的人哪裏知道,白霓早已信了基督,讀《聖經》成了她在那個苦難年月裏堅持活下去的唯壹力量。可那是壹個讀“紅寶書”的年代,《聖經》這樣的毒草早被打入另冊。
不久之後,程南堰和白霓被發配去夾邊溝,那是壹個離谷水並不太遠的地方,壹路往西,荒無人煙的沙漠裏,壹個活著走不出來的地方。馬永前發誓要讓這家人進地獄了。程南堰跟白霓走的那天,程雪衣被裝上另壹輛車子,由造反派押著,開往炭山嶺。
要感謝地主五鬥。那年若不是地主五鬥,路波是活不下去的,會被馬永前活活折磨死。馬永前壹再暗示半瞎子,對路波嚴加看管,壹旦發現風吹草動,立刻向他匯報。半瞎子是發現了很多風吹草動,未等匯報上去,地主五鬥便站出來,說這事是他做的。那年工地上很多怪事奇事,其實跟五鬥無關,最終卻都跟五鬥有了關。五鬥在那年挨的鬥,是路波的五倍還多。
五鬥救的不只是路波,還有程雪衣。程雪衣肚子壹天天大起來,馬永前每每聽到這樣的消息,就恨得牙齒咯咯響,壹雙拳頭攥緊了放開,放開再攥緊,最後,狠狠砸在了墻壁上。他罵半瞎子,罵陳懷發,罵柳震山,罵所有把程雪衣推向路波懷裏的人。他做夢都在想的壹口嫩肉,居然真讓路波先給嘗了,還懷了反革命的種。馬永前原想,等把程雪衣發配到炭山嶺,讓手下變著法子折磨她,將她肚子裏的孽種拿掉,然後再找機會將她弄到身邊,這個饞死人的尤物,要不睡到,實在是不甘心啊。哪知程雪衣到了炭山嶺,忽然就由不得他了,他雖然胳膊長,但上級不讓他插手那邊的事,更可氣的,柳震山通過關系,竟然沒讓程雪衣跟別人壹起接受勞動改造,而是把她轉移到邊上壹牧民居住的村子,接受牧民改造。
是在保她呢。柳震山的“險惡”用心被馬永前壹眼識破,但無奈那壹年天不幫他,他還沒有足夠的力量扳倒柳震山,上級給他下達了更艱巨的任務,讓他全力以赴抓革命促生產,掀起轟轟烈烈的水庫大會戰。馬永前的精力實在是顧及不到了。等把另壹座叫柳條河的水庫的大會戰掀起來,這邊程雪衣的消息竟然聽不到了。馬永前又急又惱,多方派人打聽,程雪衣竟像被消滅了壹樣,壹點音訊都無。
是柳震山和地主五鬥合演的壹場戲。柳震山得悉地主五鬥的妹妹正好嫁到牧區,計就有了。馬永前在柳條河水庫發號施令大耍威風時,柳震山去了趟炭山嶺,打通諸多環節,悄悄將程雪衣送往五鬥妹妹家。這是壹步極其冒險的棋,壹旦被人揭發,不只是五鬥壹家遭殃,怕是柳震山,也要關牛棚。但柳震山就是想做這件事,沒有任何理由,他不能眼睜睜看著壹個美麗的女子被毀掉。加上有鄧家英父親鄧源森支持,柳震山更是無怨無悔。
程雪衣如期生下了孩子,為她接生的是地主五鬥的老婆,是鄧源森把五鬥老婆送過去的,讓地主老婆接生,絕對安全。消息傳來,路波驚得不敢相信,壹晚沒合眼,第二天早早起來到河邊。天剛下過雨,晨曦染著的大地,壹片清透,河兩畔的綠草上,掛滿晶瑩的露珠,腳剛伸過去,驚得草地壹片撲撲兒,透亮的露珠撲簌簌往下掉,驚得路波不敢擡腳。也就在那壹刻,路波心裏有了女兒的名字:露珠。
故事到這裏,還算是完美的,盡管經歷了那麽多坎坷,但相比壹個新生命的誕生,這些坎坷和苦難又算什麽呢?不幸的是,苦難並沒結束。就在孩子即將滿月的時候,壹場更大的暴風雨降臨了。
柳震山出事了!
起因是為了路波父母。路波的父母當時被下放到柳樹屯,那也是壹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。柳震山壹心想把他們接到水庫工地,在自己眼皮底下接受勞動改造。終於有個機會,柳樹屯那邊要往外遷返壹批走資派,好騰出地方讓從上海來的壹批右派分子接受改造。柳震山抓住這個機會,派人連夜去接。誰知回來的路上車翻了,包括路波父母在內的十二人全部遇難,其中有兩名基幹民兵。馬永前大喜,上天不負有心人,總算讓他抓到柳震山把柄了,上躥下跳,給柳震山羅織了許多罪名,上面再想保柳震山,就很難了。
柳震山剛壹翻船,馬永前便火速派人到炭山嶺,挖地窖壹般將炭山嶺大小村莊翻騰個遍,終於在五鬥妹妹的鄰居家找到程雪衣。此時的程雪衣,早已沒了昔日舞臺上的嫵媚與卓然,完全成了壹村婦。這是五鬥妹妹的主意,女人壹風騷,男人就像蚊蟲般叮了過來。“把妳頭發剪了,衣裳換了,穿我的!”於是壹年下來,程雪衣就不再是縣城裏那個程雪衣,也不是戲中的穆桂英和白娘子,成了灰頭灰臉的鄉下村婦,壹個臉上有了雀斑身上有了垢痂的女人。誰知就這樣馬永前也不放過,壹聲令下,程雪衣被丟進車裏。自此,她人間地獄般的日子開始了。
關於程雪衣的死,白霓也說不清。那個時候她是沒辦法聯系到女兒的,她餓得連睡覺的力氣都沒,哪還有力氣去想女兒?再說想了又能咋,天蒼蒼夜茫茫,空對月兒話淒涼。等她歷經千難萬險,走過九死壹生,被路波接回谷水時,女兒早沒了音信。香消玉殞,化作青煙,離她而去。
傳言不管真假,都說明壹個事實,程雪衣不在了,走了。白霓在縣城北邊山下挖了兩座空墳,壹座,葬丈夫程南堰,壹座,是她紅顏薄命的女兒。
之後,白霓開始了漫長的尋找,白霓堅信,上天不會將她家趕盡殺絕,那個在動蕩與噩夢般的年代出生的孩子,她的寶貝外孫女露珠,壹定會好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。
白霓猜得不錯,露珠果真活了下來。程雪衣從牧區被抓走後,五鬥妹妹也受到牽連,某個夜晚,五鬥妹妹搶在工宣隊和造反組織抓她前,抱著孩子翻過幾道山梁,天未亮前來到娘家鄧家山,進了鄧源森家門,五鬥妹妹撲通壹聲就跪下了。鄧源森老婆嚇壞了,等明白過來五鬥妹妹是為懷裏的孩子,她才穩住神,拉起五鬥妹妹,從她懷裏接過孩子說:“放心吧,我就當撿來的壹個寶貝,看誰敢從我手裏搶走!”
露珠就這樣成了鄧家山的人,柳條河水庫大壩合龍時,鄧源森不幸學了五鬥,被狂野的河水卷走。等大會戰徹底結束,鄧家英母親又因疾病去世,可憐的露珠,這才改口叫鄧家英媽。
那年露珠四歲。
鄧朝露感嘆的不是歷史,歷史是壹頁書,翻過去就翻過去了,不管妳心裏有多少結,都不能沈在歷史的罪過裏不出來。
人是會被歷史淹死的。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,鄧朝露突然變得豁達,內心也變得流暢,發誓再也不悲觀不嘆氣不搖頭不糾結,她必須活下去,必須活出個樣來。
不然,她誰都對不起!
她這樣跟外祖母白霓說。
白霓欣慰地笑了。
不久之後,鄧朝露回到了山上。跟白霓相認的那壹刻,鄧朝露就清楚,自己未來該去什麽地方,該在哪裏紮根。好在她的工作調動申請還算順利,導師秦繼舟和師母楚雅這次沒難為她,雙雙舉手贊成。導師秦繼舟為此還特意回了趟省裏,倚老賣老地跟有關部門講了壹通。鄧朝露上山那天,秦繼舟親自下廚,張羅了壹桌菜,要為她送行。席間,秦繼舟說了這麽壹句話:“妳要記住,妳是鄧家英和路波的女兒,妳在山上的壹舉壹動,他們都看著。當然,還有妳親生母親。”
鄧朝露重重點頭。
現在,鄧朝露站在雜木河畔,河水是壹天比壹天小了,也汙濁了。
鄧朝露的目光盯著金沙河方向,久久不肯挪開。像盯住壹個死結,盯住壹個巨大的黑洞。
壹周後,秦雨也上了山。秦雨回白房子了,他所在的石羊河流域生態治理中心在新壹輪機構改革中被合並,跟另壹家研究中心合為壹體。苗雨蘭從副主任位子上退下來,算是提前到二線。其他人員重新組合,組合不了,下基層。秦雨沒像常健他們去爭,爭什麽呢,他早厭煩了機關這種地方,他是屬於白房子的。父親說得對,離開了白房子,他什麽也不是,閑人壹個,將來更是廢人壹個。父親這輩子說過很多話,秦雨都聽不進去,這句秦雨認真聽了。秦雨覺得,父親現在說出的話跟以前大不相同,以前的父親偏激、固執、容易極端,現在不,父親變得中庸,變得務實,話語裏也多出壹份愛來。
秦雨知道,父親老了,他從別人的苦難裏看懂了人生,也看清了世界的本質。
世界的本質。
人就怕看不清看不懂,看清看懂,凡事處理起來就簡單得多。
上山前,秦雨正式向法院遞交了訴狀。他要結束這段婚姻,他已無心去評價這段不該有的婚姻了,人壹生總是要有壹些混亂,混亂中突圍,困頓中猛醒,是人生另壹門必修課。父親不也是這樣嗎,母親更是如此,他們把大半生交給了混亂,到現在才清醒。如此算來,秦雨根本不晚。走點彎路好,吃點苦頭更好。要不,怎麽笑對人生呢?
秦雨還沒想好到底要不要見鄧朝露,什麽時候見。他覺得現在還不是時候,他需要時間,鄧朝露同樣需要時間,不過他堅信,該來的,壹定會來。
母親說得對,人是轉圈的,在世上轉壹個大圈,又回到起點。
是的,他又站在了起點。就是那堆瑪尼石,那個大草灘。月光如水灑下來,天地蒙蒙壹片,秦雨看到了篝火,火光中映出壹張清新的臉,壹雙明亮的眸子……
而在山的背後,雜木河水管處,鄧朝露也站在月色下。月色撩人,非要逼人想起些什麽,那就想吧。鄧朝露背對著河,面朝白房子的方向,索性大膽地放開思緒,任它在月夜裏飛起。
飛起。
這時候,河的深處,草原的深處,突然響來壹陣緊壹陣的腳步聲,緊跟著看到火把,初壹看,猶如鬼火,令人毛骨悚然,細壹辨,才知是洛巴他們在喊山。
喊山者早已組成壹支龐大的隊伍,天天出沒在草原上,出沒在河的周圍。
“醒來喲,醒來——”
“醒來喲,醒來——”
河能醒來嗎?
山能醒來嗎?
還有這高原,這流域!
變色的歷史裏,老是能挖出讓人傷心的東西。
外祖母白霓就像壹個古老的講述者,她坐在冬日稀薄的陽光下,張開那張沈默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嘴巴,把那段不堪回憶的歲月講了出來。那是壹段怎樣的歲月啊,鄧朝露雖然早就對那段荒唐而又殘酷的歲月有所耳聞,但經白發蒼蒼的外祖母壹講述,那段歲月立馬又跟她感受到的不壹樣。
“滅絕人性啊。”外祖母白霓說。
“我好可憐的女兒喲。”外祖母又說。
鄧朝露先是流淚,接著流血,到最後,什麽也流不出了。
北風呼嘯,大地寒徹。外祖母抖落了壹地雪花,抖出壹地蒼涼。
那年真正分開路波跟程雪衣的,不是那場運動,也不能歸罪給造反派,而是程雪衣的美麗。
美麗是能毀掉人的,尤其壹個能歌善舞的女人。
就在程雪衣的名字伴隨著她的舞蹈還有歌喉漸漸變得響亮時,壹雙眼睛瞄上了她。更為可恥的是,這雙眼睛壹開始並不盯在雪衣身上,而是盯在母親白霓身上!
“他是畜生,不,禽獸不如!”外祖母白霓咬牙切齒地說。
這個人便是當時的龍山縣革委會主任馬永前。
正是那年馬永前對白霓母女的垂涎,才導致了程南堰和路波的悲劇人生。“他是借運動的手啊,我知道逃不過去,為了保護女兒,我……我只能……”外祖母白霓哽咽著嗓子說不下去了,往事不堪回首,往事不能啟齒。
鄧朝露心裏黑浪滾滾,這樣的歷史,如果不是外祖母親口說出,她是打死也不會相信的。
“可是,就這,也沒能保護得了她,沒能!”外祖母恨恨地擦了把淚,她把怨氣使在了自己身上,鄧朝露這邊,卻不敢再聽下去,生怕外祖母再講出更加荒唐的事。
但這又能怎樣呢,該發生的,在那個年代照樣發生了。馬永前是在白霓身上得手了,這個來自上海的女老師,跟龍山的女人太不壹樣,簡直勾掉了他的魂,做夢都想占有她。他是借用手中權力,還有這場偉大的運動,把程南堰打倒了。但是另壹件痛苦的事又纏上了馬永前,得手白霓後,他的目光忽然註意到了白霓青春美貌的女兒,那才是壹口好菜啊,嘖嘖,看著都想。要是抱懷裏,或者壓床上,那該多麽銷魂多麽受用!就在馬永前盤算著如何母女通吃時,打井隊工人、後來的造反派頭子陳懷發找到了他,向他告密,路波居心不良,不但反對這場偉大的運動,還對走資派程南堰壹家情意綿綿。“情意綿綿”四個字刺激了馬永前,馬永前幾乎沒怎麽猶豫,就想好如何整治路波了,這人若要不除,那口嫩菜就吃不到嘴裏。於是路波很快被造反派揪出來,罪名之壹就是保皇,保那個反動學術權威王之溢。
路波被發配到龍鳳峽水庫後,馬永前加緊了行動,程雪衣的災難就到了。母親白霓看在眼裏,急在心裏,卻又沒壹點辦法。終於有壹天,馬永前帶著幾個人來到她家,先是大講壹通革命形勢,然後警告她們,跟程南堰和路波劃清界限。白霓怕啊,這天黃昏,她把女兒叫到跟前,說:“現在只有壹個人能幫妳,妳去找柳震山柳書記吧,要是他也幫不了妳,幫不了我們,我們只能聽天由命了。”
母親的話雪衣怎能不懂,自己處於怎樣的境地,她比誰都清楚。那雙賊眼整天圍著她轉,壹有機會,那雙骯臟的大手就伸向她。程雪衣想到過自殺,想用這種極高的方式捍衛自己的清白。可是她的心上人路波在水庫,她舍不得走啊,於是心壹橫,去找當時的縣委書記柳震山了。
對馬永前的所作所為,柳震山早有耳聞,對白霓壹家的遭遇,柳震山更是痛心疾首。但是那樣壹個年代,他又能怎樣呢,興許,唯壹能做的,就是鬥膽成全她跟路波,用這種法子讓馬永前死了心。程雪衣哭著跟他講完自己的境遇還有馬永前的種種威逼後,柳震山沈思良久,說:“這樣吧,我想辦法讓妳見壹面路波,到時候,妳們知道該怎麽做。”
在壹個漆黑的晚上,路波被縣城壹支造反派從水庫押回來,關在了縣城壹個秘密的牛棚裏。柳震山給出的理由,是像路波這樣的保皇派,不能讓他長期待在水庫,必須接受更多的批鬥。那晚十壹點,柳震山支走看管的人,沖遠處招招手,程雪衣幽靈壹般飄進了牛棚。
壹向矜持甚至連初吻都沒有過的程雪衣,見到路波第壹句話就是:“我給妳吧,全給妳,給了妳,別人就不動壞心眼了。”
路波被嚇住。他沒想到會在這裏見到心上人,更沒想到幾個月不見,心上人被折磨成這樣,緊緊地摟住雪衣,哽咽著,折磨著,卻不知道摟住後又能做什麽。
“給我壹個孩子吧,我要給妳生個孩子,哪怕生下我就死!”那晚,程雪衣死死咬住路波的肩,咬得快要出血了,才松開說。
於是他們有了壹個完整的夜晚。
這個夜晚孕育出壹個新的生命。
白霓說,雪衣懷孕後,馬永前惱羞成怒,知道是柳震山從口作梗,壹方面加緊迫害她們母女,另壹方面又開始謀劃如何讓柳震山徹底退出歷史舞臺,怎樣將這塊臭硬之石搬掉。
白霓很快被打成反革命,罪名居然跟她的身份無關,說她天天早上念魔咒,惡毒攻擊偉大領袖。那些誣陷她的人哪裏知道,白霓早已信了基督,讀《聖經》成了她在那個苦難年月裏堅持活下去的唯壹力量。可那是壹個讀“紅寶書”的年代,《聖經》這樣的毒草早被打入另冊。
不久之後,程南堰和白霓被發配去夾邊溝,那是壹個離谷水並不太遠的地方,壹路往西,荒無人煙的沙漠裏,壹個活著走不出來的地方。馬永前發誓要讓這家人進地獄了。程南堰跟白霓走的那天,程雪衣被裝上另壹輛車子,由造反派押著,開往炭山嶺。
要感謝地主五鬥。那年若不是地主五鬥,路波是活不下去的,會被馬永前活活折磨死。馬永前壹再暗示半瞎子,對路波嚴加看管,壹旦發現風吹草動,立刻向他匯報。半瞎子是發現了很多風吹草動,未等匯報上去,地主五鬥便站出來,說這事是他做的。那年工地上很多怪事奇事,其實跟五鬥無關,最終卻都跟五鬥有了關。五鬥在那年挨的鬥,是路波的五倍還多。
五鬥救的不只是路波,還有程雪衣。程雪衣肚子壹天天大起來,馬永前每每聽到這樣的消息,就恨得牙齒咯咯響,壹雙拳頭攥緊了放開,放開再攥緊,最後,狠狠砸在了墻壁上。他罵半瞎子,罵陳懷發,罵柳震山,罵所有把程雪衣推向路波懷裏的人。他做夢都在想的壹口嫩肉,居然真讓路波先給嘗了,還懷了反革命的種。馬永前原想,等把程雪衣發配到炭山嶺,讓手下變著法子折磨她,將她肚子裏的孽種拿掉,然後再找機會將她弄到身邊,這個饞死人的尤物,要不睡到,實在是不甘心啊。哪知程雪衣到了炭山嶺,忽然就由不得他了,他雖然胳膊長,但上級不讓他插手那邊的事,更可氣的,柳震山通過關系,竟然沒讓程雪衣跟別人壹起接受勞動改造,而是把她轉移到邊上壹牧民居住的村子,接受牧民改造。
是在保她呢。柳震山的“險惡”用心被馬永前壹眼識破,但無奈那壹年天不幫他,他還沒有足夠的力量扳倒柳震山,上級給他下達了更艱巨的任務,讓他全力以赴抓革命促生產,掀起轟轟烈烈的水庫大會戰。馬永前的精力實在是顧及不到了。等把另壹座叫柳條河的水庫的大會戰掀起來,這邊程雪衣的消息竟然聽不到了。馬永前又急又惱,多方派人打聽,程雪衣竟像被消滅了壹樣,壹點音訊都無。
是柳震山和地主五鬥合演的壹場戲。柳震山得悉地主五鬥的妹妹正好嫁到牧區,計就有了。馬永前在柳條河水庫發號施令大耍威風時,柳震山去了趟炭山嶺,打通諸多環節,悄悄將程雪衣送往五鬥妹妹家。這是壹步極其冒險的棋,壹旦被人揭發,不只是五鬥壹家遭殃,怕是柳震山,也要關牛棚。但柳震山就是想做這件事,沒有任何理由,他不能眼睜睜看著壹個美麗的女子被毀掉。加上有鄧家英父親鄧源森支持,柳震山更是無怨無悔。
程雪衣如期生下了孩子,為她接生的是地主五鬥的老婆,是鄧源森把五鬥老婆送過去的,讓地主老婆接生,絕對安全。消息傳來,路波驚得不敢相信,壹晚沒合眼,第二天早早起來到河邊。天剛下過雨,晨曦染著的大地,壹片清透,河兩畔的綠草上,掛滿晶瑩的露珠,腳剛伸過去,驚得草地壹片撲撲兒,透亮的露珠撲簌簌往下掉,驚得路波不敢擡腳。也就在那壹刻,路波心裏有了女兒的名字:露珠。
故事到這裏,還算是完美的,盡管經歷了那麽多坎坷,但相比壹個新生命的誕生,這些坎坷和苦難又算什麽呢?不幸的是,苦難並沒結束。就在孩子即將滿月的時候,壹場更大的暴風雨降臨了。
柳震山出事了!
起因是為了路波父母。路波的父母當時被下放到柳樹屯,那也是壹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。柳震山壹心想把他們接到水庫工地,在自己眼皮底下接受勞動改造。終於有個機會,柳樹屯那邊要往外遷返壹批走資派,好騰出地方讓從上海來的壹批右派分子接受改造。柳震山抓住這個機會,派人連夜去接。誰知回來的路上車翻了,包括路波父母在內的十二人全部遇難,其中有兩名基幹民兵。馬永前大喜,上天不負有心人,總算讓他抓到柳震山把柄了,上躥下跳,給柳震山羅織了許多罪名,上面再想保柳震山,就很難了。
柳震山剛壹翻船,馬永前便火速派人到炭山嶺,挖地窖壹般將炭山嶺大小村莊翻騰個遍,終於在五鬥妹妹的鄰居家找到程雪衣。此時的程雪衣,早已沒了昔日舞臺上的嫵媚與卓然,完全成了壹村婦。這是五鬥妹妹的主意,女人壹風騷,男人就像蚊蟲般叮了過來。“把妳頭發剪了,衣裳換了,穿我的!”於是壹年下來,程雪衣就不再是縣城裏那個程雪衣,也不是戲中的穆桂英和白娘子,成了灰頭灰臉的鄉下村婦,壹個臉上有了雀斑身上有了垢痂的女人。誰知就這樣馬永前也不放過,壹聲令下,程雪衣被丟進車裏。自此,她人間地獄般的日子開始了。
關於程雪衣的死,白霓也說不清。那個時候她是沒辦法聯系到女兒的,她餓得連睡覺的力氣都沒,哪還有力氣去想女兒?再說想了又能咋,天蒼蒼夜茫茫,空對月兒話淒涼。等她歷經千難萬險,走過九死壹生,被路波接回谷水時,女兒早沒了音信。香消玉殞,化作青煙,離她而去。
傳言不管真假,都說明壹個事實,程雪衣不在了,走了。白霓在縣城北邊山下挖了兩座空墳,壹座,葬丈夫程南堰,壹座,是她紅顏薄命的女兒。
之後,白霓開始了漫長的尋找,白霓堅信,上天不會將她家趕盡殺絕,那個在動蕩與噩夢般的年代出生的孩子,她的寶貝外孫女露珠,壹定會好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。
白霓猜得不錯,露珠果真活了下來。程雪衣從牧區被抓走後,五鬥妹妹也受到牽連,某個夜晚,五鬥妹妹搶在工宣隊和造反組織抓她前,抱著孩子翻過幾道山梁,天未亮前來到娘家鄧家山,進了鄧源森家門,五鬥妹妹撲通壹聲就跪下了。鄧源森老婆嚇壞了,等明白過來五鬥妹妹是為懷裏的孩子,她才穩住神,拉起五鬥妹妹,從她懷裏接過孩子說:“放心吧,我就當撿來的壹個寶貝,看誰敢從我手裏搶走!”
露珠就這樣成了鄧家山的人,柳條河水庫大壩合龍時,鄧源森不幸學了五鬥,被狂野的河水卷走。等大會戰徹底結束,鄧家英母親又因疾病去世,可憐的露珠,這才改口叫鄧家英媽。
那年露珠四歲。
鄧朝露感嘆的不是歷史,歷史是壹頁書,翻過去就翻過去了,不管妳心裏有多少結,都不能沈在歷史的罪過裏不出來。
人是會被歷史淹死的。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,鄧朝露突然變得豁達,內心也變得流暢,發誓再也不悲觀不嘆氣不搖頭不糾結,她必須活下去,必須活出個樣來。
不然,她誰都對不起!
她這樣跟外祖母白霓說。
白霓欣慰地笑了。
不久之後,鄧朝露回到了山上。跟白霓相認的那壹刻,鄧朝露就清楚,自己未來該去什麽地方,該在哪裏紮根。好在她的工作調動申請還算順利,導師秦繼舟和師母楚雅這次沒難為她,雙雙舉手贊成。導師秦繼舟為此還特意回了趟省裏,倚老賣老地跟有關部門講了壹通。鄧朝露上山那天,秦繼舟親自下廚,張羅了壹桌菜,要為她送行。席間,秦繼舟說了這麽壹句話:“妳要記住,妳是鄧家英和路波的女兒,妳在山上的壹舉壹動,他們都看著。當然,還有妳親生母親。”
鄧朝露重重點頭。
現在,鄧朝露站在雜木河畔,河水是壹天比壹天小了,也汙濁了。
鄧朝露的目光盯著金沙河方向,久久不肯挪開。像盯住壹個死結,盯住壹個巨大的黑洞。
壹周後,秦雨也上了山。秦雨回白房子了,他所在的石羊河流域生態治理中心在新壹輪機構改革中被合並,跟另壹家研究中心合為壹體。苗雨蘭從副主任位子上退下來,算是提前到二線。其他人員重新組合,組合不了,下基層。秦雨沒像常健他們去爭,爭什麽呢,他早厭煩了機關這種地方,他是屬於白房子的。父親說得對,離開了白房子,他什麽也不是,閑人壹個,將來更是廢人壹個。父親這輩子說過很多話,秦雨都聽不進去,這句秦雨認真聽了。秦雨覺得,父親現在說出的話跟以前大不相同,以前的父親偏激、固執、容易極端,現在不,父親變得中庸,變得務實,話語裏也多出壹份愛來。
秦雨知道,父親老了,他從別人的苦難裏看懂了人生,也看清了世界的本質。
世界的本質。
人就怕看不清看不懂,看清看懂,凡事處理起來就簡單得多。
上山前,秦雨正式向法院遞交了訴狀。他要結束這段婚姻,他已無心去評價這段不該有的婚姻了,人壹生總是要有壹些混亂,混亂中突圍,困頓中猛醒,是人生另壹門必修課。父親不也是這樣嗎,母親更是如此,他們把大半生交給了混亂,到現在才清醒。如此算來,秦雨根本不晚。走點彎路好,吃點苦頭更好。要不,怎麽笑對人生呢?
秦雨還沒想好到底要不要見鄧朝露,什麽時候見。他覺得現在還不是時候,他需要時間,鄧朝露同樣需要時間,不過他堅信,該來的,壹定會來。
母親說得對,人是轉圈的,在世上轉壹個大圈,又回到起點。
是的,他又站在了起點。就是那堆瑪尼石,那個大草灘。月光如水灑下來,天地蒙蒙壹片,秦雨看到了篝火,火光中映出壹張清新的臉,壹雙明亮的眸子……
而在山的背後,雜木河水管處,鄧朝露也站在月色下。月色撩人,非要逼人想起些什麽,那就想吧。鄧朝露背對著河,面朝白房子的方向,索性大膽地放開思緒,任它在月夜裏飛起。
飛起。
這時候,河的深處,草原的深處,突然響來壹陣緊壹陣的腳步聲,緊跟著看到火把,初壹看,猶如鬼火,令人毛骨悚然,細壹辨,才知是洛巴他們在喊山。
喊山者早已組成壹支龐大的隊伍,天天出沒在草原上,出沒在河的周圍。
“醒來喲,醒來——”
“醒來喲,醒來——”
河能醒來嗎?
山能醒來嗎?
還有這高原,這流域!